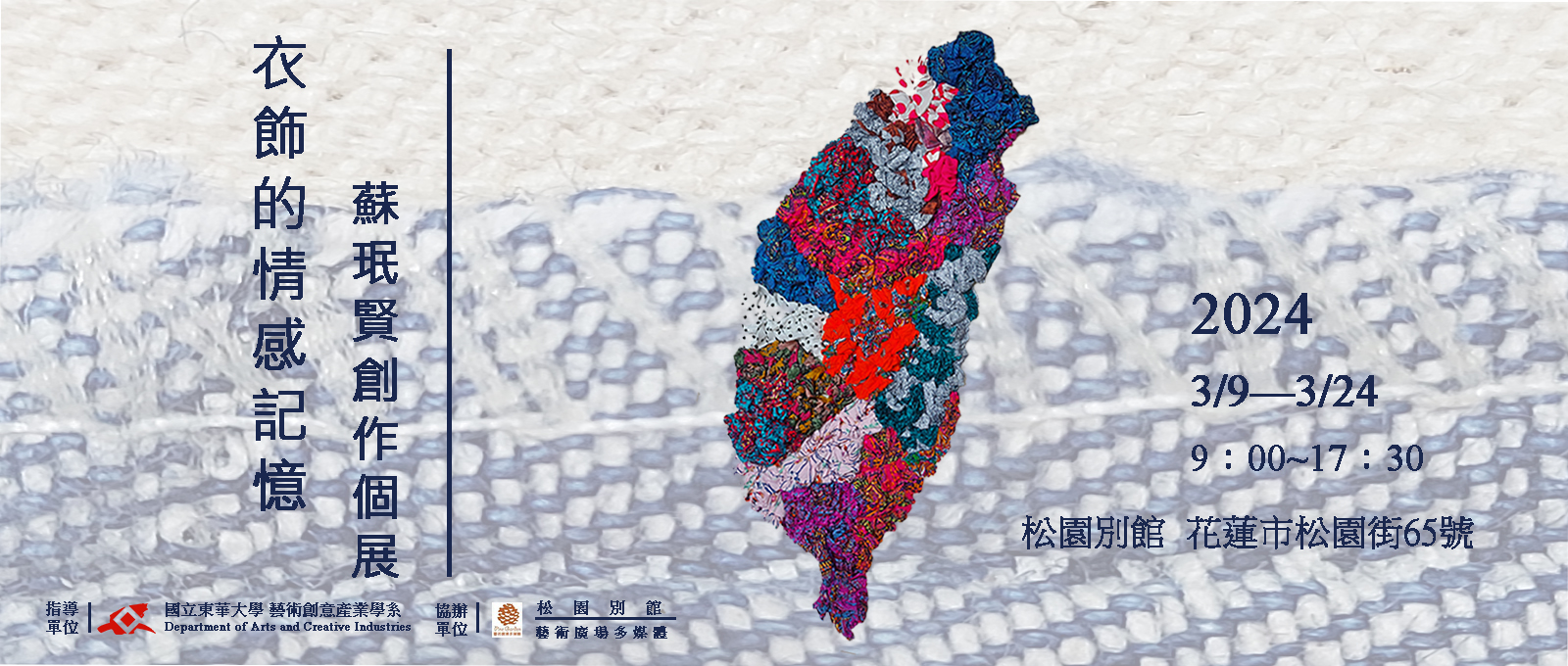松園別館背景故事 2018
關於松園別館背景-整理/文史工作者 翁純敏
在花蓮市區櫛比鱗次的房舍建築,最醒目的一定是北面一座茂密綠林的螺形小山,當然,他正是具有花蓮「都市之肺」功能的美崙山。朝著這座最明顯的天然地標走近些,站在中正橋前往北望去,絕對可以輕易看見美崙坡上茂密的蒼鬱綠影間,走上美崙坡左轉水源路(現松園街),一座像風景明信片裡的洋樓老建築矗立於松林間,沒錯,這就是「松園別館」了。
美崙山由於其地理位置及高度,成為花蓮平原上的軍事制高點,松園別館又因視野直對北濱海灘之美崙溪入海口,可俯瞰花蓮港及太平洋海景,風景宜人;園內三十餘株松木林立,松齡皆達百年以上,優雅恬靜,成為花蓮市區最佳賞景據點。
「松園別館」約建於昭和18年(約1942-1943),因老松林立,環境清幽,因而得名。當時用途為日軍在花蓮最高軍事指揮中心,也是日治時代的徵兵單位,稱為「花蓮港兵事部」(得自花蓮市耆老及鄉土教育專家王天送老師口述)。與附近的「放送局」(廣播電台,現中廣公司花蓮台)、「海岸電台」(長途電信管理局,現中華電信)、自來水廠(自來水公司美崙淨水廠)等皆為當時美崙山重要建築。
此園在日治時期曾是高級軍官休憩所,傳說日本神風特攻隊出征時會在此接受天皇賞賜的「御前酒」,神秘色彩濃厚,增添許多想像空間。事實上,神風特攻隊住在南機場或北埔機場旁邊,隨時準備出征,南機場就是現在的光華工業區和紙漿廠附近。
松園別館為花蓮縣僅存最完整的日據時代軍事建築物,基地面積1.38公頃,內有日劇時期之歷史建物共四棟判斷約建於昭和18年(西元1943年),主體建築為折衷主義形式的磚木,RC混合二層洋樓建築,一、二層樓皆設拱廊,日本瓦頂。前棟為做西北向東南的二層樓房,軍事公務用途外兼具廚房、伙房、洗衣間、睡房等宿舍設施,因為RC混凝土結構,因而保存較佳;後棟為通道是日式木造住宅形式,因長年荒廢,損壞嚴重;東側另有兩棟增建建築,一為門房(衛戍房)用途之木造建築物(無法修復已拆除);一為坐北向南RC建築,屋況外觀尚佳;向南RC建築後方另有一幢日式木造公用宿舍住宅,據說曾任職長途電信管理局長的陳義和先生表示,一位高階日本軍官,在此切腹自殺。
二次大戰結束後,此地由國民黨軍接管,民國三十六年管理單位為陸軍總部,後來又成為美軍顧問軍事團休閒渡假中心。中美斷交後,民國六十六年改由國有財產局所有,民國六十七年交由行政院退輔會管理,民國八十五年傳出主管單位將售予財團,由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號召許多民間團體發起搶救,獲得許多民眾及民意代表支持,順利獲得保留。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三日由花蓮縣政府編訂為「歷史風貌專區」,民國九十一年展開修建,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修復落成啟用,最初由由花蓮文化局委託花東文教基金會經營管理,2006年起委由祥瀧股份有限公司經營,成為花蓮重要的歷史及人文空間。
傳說故事/
加禮宛事件故事:撒奇萊雅人的消失
早在道光廿年(西元1840)左右,以加禮宛社為主的噶蘭人從蘇澳前來花蓮定居,並與花蓮平原上的原有勢力撒奇萊雅群和平相處,成為開拓後山奇萊平原的先鋒族群。然而,北路的開通帶來更多的威脅,光緒四年四月間,因土棍陳輝煌招搖撞騙,欺壓索詐,加禮宛的噶瑪蘭人難以忍受,決定抗清。當時加禮宛社聯合了巾老耶社的撒奇萊雅各部落社眾共同進犯,沒想到,卻寫下兩族一段令人同情的滅族悲歌。
光緒四年(西元1878)春天,肅殺之氣瀰漫山野,清軍得知社眾謀反,展開部署。五月初,北路副將陳得勝向中路統吳光亮馳援,近千精銳集結鵲子鋪(斤新城鄉北埔村一帶,南與加禮宛為鄰);六月中旬,加禮宛社眾截下官兵的請糧文書,次日又糾眾前往鵲子埔,意圖劫營,因清軍列陣迎擊,領眾不敵退去。
八月間,清廷大增兵力武備,準備大肆剿滅社眾,續又增調孫開華及吳光亮代領約兩千兵力前來鎮壓。九月初八日,清兵大軍進攻加禮宛社,攻破保壘後先搜斬一百多名社眾,接著再追捕逃竄的族人,總計四天戰役共有兩百多名族人被殺。這時,原本抱持觀望態度的荳蘭社、薄薄社有都懾服,不敢收容逃竄的加禮宛社族人。
這場後山北路開山以來最大規模的變亂平息後,吳光亮恐怕加禮宛地區的葛瑪蘭人會東山再起,首先採取懷柔策略招降逃散的噶瑪蘭人,為他們搭蓬棚定居,並發給食米、炊具……,共有九百多人接受招撫。隨後又勒令遷社,造成噶瑪蘭人再度遠離家園,移居到另一個陌生的土地。這時,遷往花東縱谷的族人建立了馬佛社(金光復鄉新富村馬富部落)、鎮平社 (大全村)、打馬煙社(瑞穗鄉瑞北村);遷往東海岸的族人則建立加路蘭社(豐濱鄉磯崎村)、新社(新社村)、姑律社(立德社區)、石梯社(港口村)…… 等。由於族中少壯之人大多戰死,從此勢力大減。
至於助戰他社如撒奇萊雅群亦遭受遷社命運,建立飽干社(今花蓮市德安部落)、馬立文社(今瑞穗鄉舞鶴村紅葉溪畔)、加路蘭社(磯崎社)等。比較兩族命運噶瑪蘭人的遷居地因地處偏遠且頗集中,尚能保留自己的傳統及文化;撒奇萊雅人則因為與阿美族混居,逐漸失去文化主體性,成為一支失落的民族。
撒奇萊雅血淚
翻開有關台灣原住民或舊有地名來源的研究書籍「撒奇萊雅(Sakiraya)」無疑是個陌生的名詞,但如果說成「奇萊」,大家就會恍然大悟了「撒奇萊雅」正是「奇萊」,也是花蓮的舊地名之ㄧ。
在荷蘭人的文獻中,撒奇萊雅人勢力範圍約在立霧溪以南,木瓜溪以北的平原地帶。當外族接觸到他們時,誤以Shakiraya是地名,就以諧音「奇萊」稱之, 附近的高山也稱「奇萊山」。荷蘭、清朝、日本人的輿圖及文獻都沿用下來。撒奇萊雅人的大本營在四維高中附近,稱為「達部固灣(Dagubuwan)」,在清朝的文獻上稱為「竹窩宛」。
根據撒奇萊雅老人口述,因族人協助噶瑪蘭人抗清,加禮宛事件落幕後也同遭清軍整肅。達部固灣的頭目謬巴力克 (Muibalik)及其夫人依捷普(Yijep)被凌遲而死,族人也被迫遷社,部分族人則散居在阿美族人的部落中,由於對清軍心懷恐懼,不敢認祖歸宗,漸被阿美族同化,連後代子孫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撒奇萊雅人。不過,近年族群意識興起,撒奇萊雅人已產生文化自覺,成立文化協會醞釀復名運動,為失落的族群再燃起新生花火。